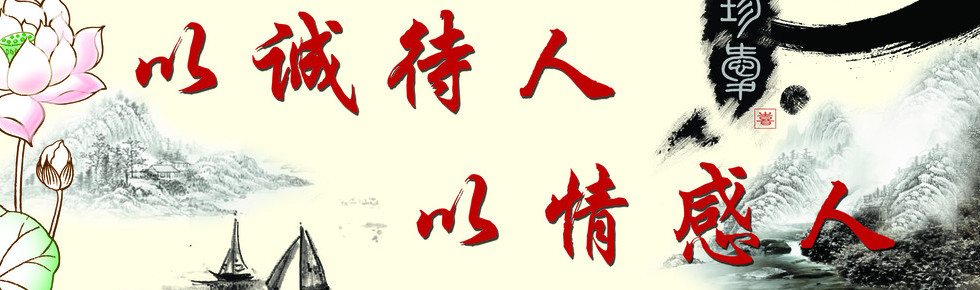年,在对心血管病患者所出现的慢性的心理忧伤进行研究后,荷兰学者德诺莱特提出了D型人格,又称为忧伤人格。这种人格有两种主要成分组成:消极情感和社会压抑。
D型人格的消极情感体现在人们长期经历着消极情感的倾向。他们会冲突、沮丧、焦虑等,并且这些情绪会稳定的长期存在,并不会受到情境和时间的影响。他们会用消极情感看待自我,对负性事件更加敏感。
社会压抑是D型人格个体在社会交往中压抑自己对情感和行为的表达。在社交过程中,他们会感觉到紧张、不安全,有意识的自我压抑。表面上极其平静,内心中却极力控制自我表达,总是在交往中和别人保持距离。
以往的研究认为消极情感会加重患者的身体症状,而社会压抑会使得心脏的不良反应增加,心脏复原力减弱,心率变化增加,长此以往会导致动脉粥样硬化,从而患上冠心病。
在这个过程中,D型人格和心血管疾病的作用模型中,负性情感和压抑应对在这个模型中承担了中介变量的作用。所谓中介变量就是连接两个变量之间的桥梁。压抑的情感使得个体不能应对负性事件,长此以往,形成长期的慢性的应激状态,影响了心血管系统的正常运行。年,哈勃拉等学者对D型人格与心血管疾病和可的松反应性的关系做了一定的研究。我们一起来看看结论如何。
实验选择了名大学生作为被试,其中男性86人,女性87人,平均年龄20.4岁。实际上,这样的被试选择是有一定问题的。大学生群体普遍年轻化,患有心血管疾病的概率较低,这样的被试做出来的结果也许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且在后面结论部分,我们会发现由于被试的选择存在问题,得出的结论也有些站不住脚。
来看一看研究者收集被试的指标,其中一方面是心理指标,被试做了一份《D型人格问卷》测量,我们之前提到D型人格的两个部分包括消极情感和社会压抑,同理,这份问卷也具有这两个维度。与此同时,在实验的各个阶段,收集被试的即时情绪,包括快乐、愤怒、悲伤、恐惧、厌恶和惊讶。
生理指标的采集主要是测量心率、舒张压和收缩压以及唾液中的可的松浓度。实际上,过量的可的松可能会引发心肌损伤和ECG的变化。这是一个非常容易观测的身体变化的指标。
实验分三个阶段进行:基线阶段、任务阶段和恢复阶段。所谓基线阶段就是收集被试在平时的生理指标水平,作为参考。这个阶段会收集被试的心率、舒张压以及收缩压,并且取平均值。同时采集被试的唾液,测量其中可的松浓度,这是基线值。
在任务阶段,被试要开始经历实验者为他们精心安排的应激环节。此时被试需要完成连续减7的心算任务,并且做得越快越好的被试会得到50美元的奖励。与此同时,研究者会用言行激惹被试。其目的就是为了测试被试在这种刺激性事件下的应急反应。此时,收集被试在一定时间下的心率、舒张压和收缩压等生理指标,和唾液样本中的可的松浓度。之后是20分钟的恢复阶段。
研究者对收集到的生理指标和心理指标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他们发现,D型人格的社会压抑与应激引起的收缩压的增加呈正相关。在男性中,D型人格的消极情感与应激引起的心率增加呈现正相关。而社会压抑和消极情感都与应激所引起的可的松浓度增加有正相关关系。由此,研究者认为D型人格个体会有较高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这与他们在应对应激时较高的生理指标和可的松反应性有关。
至此,我们似乎可以看出来D型人格个体在面对应激事件时以消极的应对方式面对是很有可能患上心血管疾病的。实际上,这样的结果并不是很令人信服。
在实验被试选择上,研究者只选择了年轻的大学生,实际上,这样的群体并不能真正的表现心血管疾病患者真实的患病情况。
其次,实验设计中,研究者并未设立对照组,这使得研究者最后所得到的数据无法得到对比,排除额外变量对实验的种种影响,以至于其结论并不是很令人信服。
最后,数据处理上,研究者采用的是计算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的数据分析方法,这种方法对于实验类研究的数据分析是远远不够的。相关分析来源于达尔文的表弟高尔顿。高尔顿的“回归法”被他的学生,现代统计科学之父皮尔逊,发展出了“皮尔逊积差相关”统计法。相关关系是描述两者关系趋向的统计方法。本实验的分析认为D型人格的特质与生理指标呈现正相关,所谓正相关就是两个变量的发展趋势相同,即一个变量增加或减少,另一个变量也随着前者同向变化。实际上,相关分析只是分析两者之间的发展趋势的分析,并不能说明相关性高即因果性高。实验法是验证因果关系最佳的方法,而采用相关分析并不能说明验证因果。统计方法的选择是本实验研究的一大败笔。
实际上,临床观察发现,在排除了一系列危险因素之后,D型人格的死亡率依旧高于常人,且更容易复发心血管疾病。D型人格的消极应对方式会导致他们即使没有患病,也会有更多的痛苦体验、躯体症状和不健康行为。如果您发现自己偏向于D型人格的行为特点,那就需要努力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和心态,以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