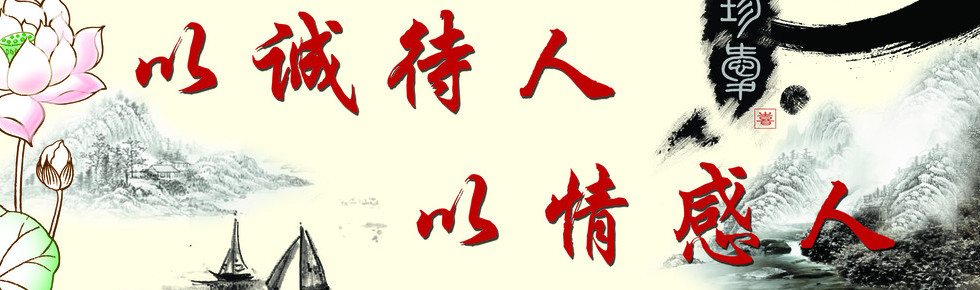最近讨论得很火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北大新生入学心理测试的调查,结果表明,近乎四成的学生存在“心理问题”,主要在于“认为人生无意义”,于是专家们将其归结为现代人的“空心病”。
回想起我刚进入华东师大的时候,也因为测试结果“不理想”而被约谈,我告诉咨询师,他们的题目太幼稚,我完全可以根据需要答出他们想要的结果,但还是根据意愿答成了一个“问题新生”。咨询师听闻后颇为尴尬,解释说:“你为什么觉得我们有一个想要的结果呢?这个测试只是想了解一些情况,并不能表明是否有心理问题。”
“但你们还是约谈了我,不是么?”
谁规定积极好过消极?
测试的内容无外乎一些量化指标,而我大抵都选择了反面:消极、悲观、不合群、孤独……几乎都是“抑郁症”的标签。
但是是谁规定,积极就好过消极、乐观就好过悲观、合群就好过孤独的呢?它们本来只是客观人格的差异表现,却被主流群体作了优劣之分,然后怀疑“劣势”人格为“有病”。
我告诉咨询师,我不积极,是因为我看到事物的两面;我不乐观,是因为我对人世存着悲悯;我不合群,是因为我看到群体性的狂欢与迷失。这种感觉,大约就是于繁华中看到落寞,于繁花间看到凋零,既无大喜,亦无大悲,只是世事如此无可奈何的悲悯罢了。
“你有想过如何解决这种悲悯吗?”
“所以我不是上帝。”我说。
我在文学中找到了答案
“欲上青天窥皓月,偶然回首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
很喜欢王国维的这句词,这大约就是我所理解的无可奈何的悲悯,因为悲悯的最大主体与客体都是自己本身。有时我也不得不承认,这种抽离体验令人痛苦。当然,在心理医师眼里,王国维大抵逃不开是有大问题的。
后来在太阳老师的文学概论课上,他说,好的文学就是出场与入场的交替,是一种悲悯。既有入乎其中的情感体验,又有出乎其外的道德反思,以人的视角感受世间的悲喜冷暖,同时从上帝的视角来审判其是非因果。好文学的背后,始终流动交织着这样一种悲悯。座中的我如惊雷棒喝,这就是悲悯!
课后我问太阳老师,要如何解决这种悲悯呢?他说,无法解决,也不用解决。
年轻人渴望特立独行
事实上,后来与同学聊起约谈的事情,几乎所有人都对我表示羡慕,希望自己也能被约谈,觉得应该很好玩。
并不是觉得好玩,我想,在这个测试中,很少人会因为符合标准而高兴,也不会有人因为不合标准而觉得悲伤,如果二选其一,大抵后者才是年轻人所渴望的,他们寻求与众不同,张扬自我的特点,而不是努力成为一个被主流大众所认可的“正常人”和“普通人”,他们宁可“病态”,也不愿安于“常态”,尤其是当价值标准由别人来规定和测评的时候。
白癜风的前期症状白癜风扩散的症状